该名女子在脸书沉痛控诉,她去年9月在车上遭一名导演性骚扰,事后曾向时任妇女部主任许嘉恬求救,但对方态度消极,甚至反问她「当下妳为什么不跳车?」、「妳怎么没有叫出来?」、「所以呢?妳希望我做什么?」
受害女子解释,当时她坐在座位中间,根本无法跳车。陪同的同事也缓颊,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那种情况下自我保护。不料许嘉恬回应,「那妳们可以利用午休时间一个小时啊,去对面华山大草坪也好,手牵手一起练习大叫,甚至练习从我们部门大叫喊到前面民主学院。」
受害女子指出,许嘉恬之后告诉她「只要程序一启动,大家都会知道妳被性骚扰,妳也知道党部就这么小,妳的名誉可能会造成受损,妳要考量到这些后果,以及妳有没有办法承受,妳确定要我去跟媒创中心讲这件事情吗?」
主管的这番态度让她心寒了,她痛心表示:「我是带著热忱进来民进党,带著伤和遗憾离开的,我失去了眼里的那道光,直到现在仍在疗愈。」
全文如下
为时已晚但也该被好好接住的求救信
「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,好不好?很多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,如果这样的话,人就会慢慢地死掉,会死掉。」
好遗憾曾经的主管,妇女部主任许嘉恬在最该是我后盾之时,选择转身离开。时隔多月了,以为能放过自己的,近期看人选之人时又无数次的翻江倒海袭来,我又哭到差一点死掉。
而我现在才有勇气整理好思绪,好好说出来。那是一个我主责的专案,摄影团队回程的路上,导演趁著大家上厢型车,昏暗欲睡长途之际,对我实施了性骚扰。他将我的头摁上他的肩,让我靠著睡,我吓傻了,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当下的状况,他觉得我疲倦,出于关心吗?他知道我是学生,是长辈的关心吗?我竟下意识的,恐惧到将此合理化来安慰自己镇定下来:不是的,应该是我的错觉。
尔后,在一个颠簸中我借故起身,尴尬地看著他(期间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睡著),他寒暄道,累了吧,看你很疲倦,手又抚摸上我后颈,在下巴肩头与胸上游移、爱抚与按摩。我后来低头看手机试图尽我可能保持距离,而我仍感受到他炽热的视线,我不敢回头,直到他的工作室。其他团队人员在外头陆续卸器材,他抽著烟,目光不曾放过我,他邀请我进去坐坐。我忍住快哭出来的样子,但我想那时我应该很僵硬,就这么站在大厅里面,他来回巡著内外状况,又回来我身边,问我有厕所,要不要去厕所。
逃无可逃之际,我躲起来了。我一进厕所立刻反锁门,跪在边上止不住干呕,我还怕他发现有什么不对劲,拚命忍住不可发出异音,因为我听到了,他在门外的踱步,以及像提醒著他存在感的清喉声。脑子一片空白,但直觉知道我可能的下场,等不到我后怕,我在听到门外脚步声多了,才敢走出去,此时我工作还没结束。
直到上捷运回家的路上,所有紧绷神经慢慢松懈,我才颤抖的打给同事求救,我慌张到语无伦次,她好好安抚下我才能拼凑起来,现在在回忆这些,对我而言也是难受的。而之后在我们决定上报主管,当时的妇女部主任许嘉恬时,我的主任不仅第一时间总在不是重点的地方,放大我被性骚扰的细节要我做回忆陈述,也在听完后,冷冷的反问我,所以呢?妳希望我做什么?
我以为我抓到了浮木,却又是更高的骇浪。我羞愧我内疚,我为何一个专案负责不了的情绪四溢,这是在她第一时间该同理我、给我专业意见之时,给我罩下的的遮羞布。我好像不该感受难过、不该生气、不该大惊小怪,因为它就是工作,所有被否定的情绪嘎然而止。尽管最后她补上说党内也能走程序,但也就草草收尾,也未立即让我停止负责此专案,只重复著强迫我要做什么决定(尽管此时仍未跟我清楚解释完程序),她说了解后再找我谈,但我当下已失去了信任感,失望的离开了会议室。
第二次再与主管面谈,由于我情绪还在高度恐慌,同事陪我前往她所在的咖啡厅,我不知道我还会面临什么。她试图营造轻松的氛围,对我说,有时候我忘了妳还太年轻,看到妳的工作干劲总会想到我年轻的时候,然后也提到她过往选举时被性骚扰的经验,再接著问及我的这次经验,说了对我最为错愕的:那你当下为什么……不跳车?我不懂,你怎么没有叫出来?
我好想离开。同事立即委婉地告诉主任,并非所有人都能在那种情况下,有意识或者有能力去做自我保护的(在这之前跟主管说明的过程里,我也都明确说过我位于座位中间,根本无法跳车,就上高速是能跳去哪里)。而我们主任给我们的回馈却是,那妳们可以利用午休时间一个小时啊,去对面华山大草坪也好,手牵手一起练习大叫,甚至练习从我们部门大叫喊到前面民主学院。之后的闲话家常我已经超载了,任何事情好像都可以很轻松的四两拨千斤来定论,飘飘然的肉身,支离破碎的灵魂。
她又陆续找我与谈几次,她要我尽快做决定,她才能帮我。那时还在混沌与迷茫间挣扎,且听她说道,当然党内有程序,我们也可以走程序,但我相对就无法帮妳,妳也要理解我态度可能比现在在更冷漠,因为我要公正客观。
我在这态度前踌躇,但我真心不希望再出现和我一样的受害者,所以想著至少要告知媒创主任。而她后来幽幽告诉我,只是无论程序一启动,或是告知媒创主任一人也好,大家也会知道我被性骚扰,你也知道党部就这么小,你的名誉可能会造成受损,你要考量到这些后果,以及你有没有办法承受。
你确定要我去跟媒创中心讲这件事情吗?妇女部算来算去也就那几个同仁,大家想一想算一算也知道是谁。
那我知道意思了。话讲到这份上,我轻声阖上办公室的门。
至始至终,有关这件事我一通主管的关切电话皆未收到,而同事却收到了一堆电话关切,被主任问我有没有跟同事散布她的谣言。就连我可能需要的社工联系资讯,她都是传给同事,让同事转传给我的。选举结束离开后,某次我才得知,连我那时的身心就诊都可以由党部支付,而这些资讯我当时完全没有得到。我难过地告诉同事,我是带著热忱进来民进党,带著伤和遗憾离开的,我失去了眼里的那道光,直到现在仍在疗愈。
无力感越来越重,在某种大局当前的氛围与压力下,我现在才能理解与接受,我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,我压根没有错,而这绝对不是自私。前主管曾询问过我是否有被性骚扰的证据,我说我没有;可我想,我现在所陈述的这一切事实与感受,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我要撑不下去了。在溃烂之前,再痛我也想腕掉。
这次,我选择为自己勇敢。我想再次相信这个世界,相信公平,相信正义,相信人与人能被理解,而不是「我忘了妳还太年轻」:并非我太年轻所以我要承受这些「成长」,这不是为我好。
这样的人如今是党中央的副秘书长。当时高举著妇女权益旗帜的人未成为我的翁文方,我就要成为我自己的翁文方。
谢谢大家看到这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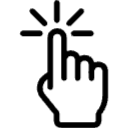 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






